霍去病是西汉著名抗匈将领,是一位少年将军。霍去病多次率军与匈奴交战,在他的带领下,匈奴被汉军杀得节节败退,霍去病也留下了“封狼居胥”的佳话,却英年早逝。永远都不要小看了中国人,我们在不经意间,数次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现在我们来说一下汉朝时发生的事。汉朝前期最主要的敌人来自于北方匈奴的威胁,刘邦甚至差点被匈奴灭了,后来出现飞将军李广,极大的威慑了匈奴,但他无力改变战局,始终处于被动防御阶段,因为一场战争的胜利,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还有创新的战法,这一点李广没有做到。
要打败匈奴,重点是骑兵问题,以步兵去对抗骑兵纯粹是找死,必先以骑兵对骑兵,深入敌境,出奇制胜,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这样一种战法是卫青发明的,但却在霍去病手中发挥出了最大的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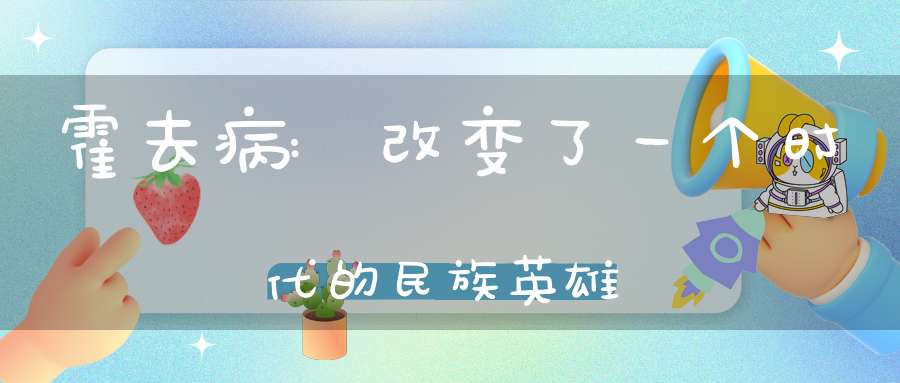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万余精锐骑兵,千里奔袭匈奴后方,6天连破匈奴五王国,斩王数名,歼敌9000人。同年第二次出击,绕河西走廊,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 远出敌后,杀敌3万余人,俘获匈奴名王5人及王母、王子、相国、将军等百余人,收降匈 奴浑邪王部众4万,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汉廷在那里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 四郡,移民实边戍守生产。
最后的漠南决战,俘虏了匈奴十万人,歼敌九万人!从此“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
欧洲战场
匈奴去了欧洲,被霍去病欺负的惨不忍睹的匈奴,其中一支残部,一路流浪到了欧洲,立刻变得威武了,直接把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西罗马帝国打得奄奄一息,西欧就此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匈奴来到欧洲之后迅速发展壮大,打完这个打那个,如入无人之境,从多瑙河一直扩张到莱茵河,文艺复兴时期的孟德斯鸠就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写道:“他摧毁了人们在这些河流沿岸所修筑的一切堡垒和工事,并且使两个帝国向他上贡”
这两个帝国,就是东西罗马,西罗马已经被打残了,自然是要上贡的,而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看见识到匈奴的威力之后,再看看自己的军队都成了战斗力不到五的渣渣,于是从423年开始,每年向匈奴上贡巨款买平安,448年又和匈奴签订了割地协议。匈奴王阿提拉几乎彻底榨干了东罗马的油水。后来,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横征暴敛也凑不够真金白银,只得可怜兮兮地给匈奴王阿提拉打了一张欠条。
再后来,匈奴把西罗马逼的穷困潦倒,再也拿不出一两银子来之后,阿提拉率军大举进攻,把整个意大利蹂躏得一塌糊涂。教皇陛下亲自出面说情,奉上大把的银子,把周边多个国家公主献上,匈奴才收兵了。在这件事的第二年,匈奴王阿拉提死了,正当欧洲人弹冠相庆,兴高采烈之时,却没想到阿拉提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王位,将整个欧洲搅得天翻地覆。
后来逼得日耳曼人举族迁徙、逃亡。一些人拉帮结伙,四处杀人越货,圈地称王。就在这样乱糟糟的时代中,西罗马帝国莫名其妙的灭亡了。欧洲现代为什么会小国林立?都是匈奴给闹腾出来的。是谁把匈奴赶到欧洲去的?大汉骠骑霍去病是也!
前几天看到有人评论霍去病,说“霍去病射杀李敢是不名誉的”,当时就想反驳几句。不过三言两语的评论很容易陷入无谓的争吵,所以就放弃了。毕竟我还见过更奇葩的观点,比如“戚继光纳妾,算什么英雄”之类的,当时不也是忍了吗?
戚继光就算纳再多的妾在当时也是合理、合法的行为,再说这跟他是民族英雄有半毛钱关系吗?
其实对历史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古今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生态、政治制度、立法基础等等都是存在差异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纳妾”的例子不值一驳,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霍去病射杀李敢事件的性质。
这就要涉及到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那就是“血亲复仇”。
看起来软踏踏的儒家,一涉及到爹娘就立马变得刚猛无比。现代人、尤其是许多年轻人对儒家的印象很糟糕,比如刻板教条,比如陈腐愚昧,比如内厉外荏等等。其实这是一种对儒家缺乏深刻认知的误解,也是对将宋明理学等同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狭隘——话说即便理学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
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后世被扭曲得太厉害,也因此被误解得太厉害
传统的儒家,非但不软弱,反而很刚猛。
比如大家现在都很熟悉的那个“以德报怨”的例子。人家孔夫子的原话是“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卷七·宪问第十四》)——啥意思呢?有恩报恩,如果有仇,那就揍他丫的!
原来印象中慈眉善目的老夫子其实也是个狠人,而且非常的愤青。
而一旦“孝悌”这个儒家伦理观的根本遭受到侵犯,老夫子和他的徒子徒孙就不止刚猛这么简单了——人家直接会爆发小宇宙,然后拎刀子找人玩命。
真正的儒生都是上马能砍人、下马能治世的全才,根本不是宋明以后的那些嘴炮弱鸡能比的
儒家认为,宗族血亲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有人对家族或成员造成伤害,那么这事肯定没完,必须报复。而且孔老夫子早就给他的徒子徒孙们立下了“祖训”: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礼记·檀弓上第三》)
啥意思呢?如果父亲被杀害了,那么当儿子的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一心一意的替父报仇就好了,如果做不到那就去死吧!哪怕是在大庭广众或是官府衙门碰到了仇人,也得当场拔刀砍死他,否则就不为人子。
在重视祖先和家族中国人看来,类似杀父这种大仇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忍的
这就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由来。而非常讲究尊卑秩序的儒家即便在复仇这件事情上,也制定了“严格”的礼仪加以限制: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礼记·曲礼上第一》)
对于杀父仇人不死不休,杀不成就自己去死;对于杀害亲兄弟者就稍微“宽容”些,逮住立刻杀掉就行了;至于杀友仇人,复仇原则上不能“跨(诸侯)国”,只能在国内追杀。
好吧,如果这也算限制的话——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如果有亲友被害,基本就不用干别的了,拎把刀整天追着仇人砍到天涯海角就好了。
在武侠等类型的影视剧中,为报父(母)仇是大侠们最常干的事
而这,就是所谓的血亲复仇。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原因在于远古时期法律不健全、执法能力也比较差劲。因此个人若要生存必须依赖于凭借血缘关系凝聚起来的宗族,而非官府。在这种情况下,血缘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赋予了血亲复仇在道德上的正义性,同时这种“自力救济”也弥补了在官府能力有限时,普罗大众对于“惩恶扬善”这一基本公平原则的普遍需要。
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本身就提供了血亲复仇的理论基础。“亲亲”、“尊尊”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通过个人行为进行复仇,被视为对于君主、亲友的基本责任,才是“忠孝节义”的体现。当然还可以拔高为维护了礼法、实现了仁义、成为了君子——《公羊传》中不就已经恶狠狠的警告过大家“不复仇,非子也”了吗?
董仲舒是儒家公羊派的代表人物,而公羊派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大复仇”
所以在那个年头,如果有人的尊长、亲友被害而无心或无力复仇,绝对是一件受人谴责和鄙视的行为。哪怕是选择“报警”,也会被视为懦弱、不孝,基本上以后就没脸出门见人了。
所以太史公才会在他的煌煌巨著《史记》中专门为刺客列传,对这种复仇行为大加颂扬。
有时候,哪怕这种血亲复仇的对象是君主,也是受到推崇和支持的:
“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旬,古之道也。”(《春秋公羊传·定公四年》)
也就是说,父亲无错被杀,儿子就可以向君主复仇;若是父亲犯罪受诛,儿子则不能寻仇——这也是孟子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思想的阐释之一。因此伍子胥叛楚投吴、回头还将楚平王掘墓鞭尸的行为,放在今天弄不好被当成“楚奸”,可在当时非但没有被儒家视为大逆不道,反而作为“烈丈夫”的典型代表而传颂千载、青史流芳。
伍子胥的复仇行为一旦跟孝悌有了关系,立马就变得光芒万丈
因此拿今天的思想观念往古人身上生搬硬套,不是闲的就是扯淡,当然更大的可能就是无知。
血亲复仇让汉朝的统治者非常头疼,但无法阻止其风行一时。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始皇帝陛下有个癖好,那就是什么玩意都想“统一一下哈”。所以在他被荆轲这家伙刺杀过一回以后,就对当时已经泛滥成灾的各种复仇行为深恶痛绝,便立法对此统统禁绝之。不过大秦朝很快完蛋,汉朝虽然偷偷摸摸的几乎全盘沿袭了前朝旧制,但在面子上还要对“暴秦恶法”欲拒还迎,于是很快便在血亲复仇这一问题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毕竟皇帝和国法的尊严要维护,而当时的儒家又大力鼓吹血亲复仇的正义性(比如董仲舒就是儒家公羊派“大复仇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其天人感应学说甚至可以认为是对皇帝的一种“复仇”行径),所以造成汉朝政府对于此类案件的判罚持自相矛盾的态度,同时也造成血亲复仇的事件屡禁不绝。
汉儒是非常生猛和激进的,绝非他们后来那些不肖子孙的德性
比如东汉时有一个叫赵娥的女子,父亲被李寿杀死,所以当她与仇人相逢时便毫不犹豫的抽刀杀之,然后割下首级去官府自首。这下子整个大汉都“高潮”了——当地的乡民蜂拥而至县衙为其鼓与呼,县长在国法与人情间无法取舍,干脆挂印辞职,看管监狱的守尉更是觉得肮脏的大牢根本不配容纳赵娥这样的孝女,非要把她撵走不可……
事情传开后,当地的郡太守、州刺史立即上表朝廷,非但认为赵娥无罪,还要给她刻碑以彰烈义,否则就跟皇帝没完;赵娥她家也成了“网红”景点,各地人士纷纷慕名而来,或是献上礼物或是只求一睹这位“女孩子”的真容;黄门侍郎梁宽、大名士傅玄为她立传、赋诗,范晔后来更是郑重其事的将赵娥的事迹列入《后汉书·列女传》。
汉灵帝刘宏要是不想被吐一脸唾沫或是被指倒行逆施,也只好将汉律当成破抹布丢一边,下诏赵娥无罪,还得捏着鼻子加以表彰。
赵娥这种女汉子,大多只能存在于汉唐这样大气磅礴的时代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淮南王刘长因辟阳侯审食其未救护其母,以袖藏铁椎击杀之;比如名士魏朗因其兄为乡人所杀,于是怀揣利刃在街上转悠了100多天,终于将仇人杀死后逃亡等等。这种行为往往因为受到舆论的推崇和公众的支持,使得官府根本无从治罪。
而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血亲复仇甚至能成为杀官造反的正当理由:
“琅邪海曲有吕母者,子为县吏,犯小罪,(县)宰论杀之。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执县宰……母曰:‘吾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遂斩之。”
正所谓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大复仇主义在汉朝如此流行,而且舆论还普遍持支持、鼓励的态度,所以就催生了一个势力庞大的需求供给方,那就是“大侠”。两汉的游侠、刺客虽然屡遭官方打击,但在民间的口碑却非常好,其中郭解、剧孟之类的佼佼者甚至因为经常替人调解纠纷或是报仇,竟然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名流。这帮家伙不但信誉比官府还好,甚至被太史公赞为“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更有甚者,当时在洛阳等地还出现了专职替人报仇的企业化组织——会任之家,网罗了数千杀手、刺客,只要有人需要复仇却力有未逮,那么自有专业人士替其解忧。
像郭解这种早该被砍头一百回的家伙,居然在当时还成了名流……
而且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信誉卓著,童叟无欺……
这种公然的复仇行为对于大汉朝廷维护统治自然是不利的,自然要制定法令予以禁止。比如东汉名臣桓谭就曾给光武帝刘秀上书,要求对这样的行为予以严惩:
“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后汉书·卷二十八上·列传第十八上》)
既然是“旧令”,则说明禁止复仇的法令早已有之,只是“然并卵”而已。在两汉的司法实践中,血亲复仇非但未受到严厉的惩戒,反而经常受到官方的包容甚至鼓励。比如汉末的阳球,因为有个官员在言谈中辱及其母,便纠集数十人杀其全家。结果他非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因此成名被举为孝廉,从此在官场上一帆风顺,最后官至尚书令、司隶校尉、卫尉。
阳球虽是酷吏,但诛杀了十常侍之一的王甫
所以说打着复仇的名义行杀人之事,在两汉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官府就算想惩处也往往无能为力,行私刑者往往还能名利双收。
汉唐盛世源远流长,也是名人辈出的时代,今天为大家呈现的就是霍去病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霍去病,汉族,河东平阳人,西汉名将,军事家,民族英雄。官拜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其父为霍仲孺,只因霍去病是霍仲孺的私生子,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直到成为骠骑将军才与父亲相认,后来将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带进宫中。并得到汉武帝的信任,称为一代权臣。霍去病自幼善骑射,练就一身好武艺,汉武帝很喜欢他,让他做近臣侍中,汉武帝还曾想亲自教授霍去病《孙子兵法》。
十七岁的霍去病被汉武帝任命为票姚校尉,随卫青征战沙场。由于霍去病刚刚开始参战,卫青让其统领八百精骑,但是霍去病做了大胆的决定,以八百精锐骑兵突袭匈奴的一个大营。匈奴未做防范,被霍去病打的措手不及,斩获敌人2028人,其中包括相国、当户等高级官员,同时也斩杀了单于的祖父辈籍若侯产(籍若侯乃封号,名产),并且俘虏了单于的叔父罗姑比,两次功冠全军,以一千六百户受封冠军侯。
十九岁被汉武帝任命为骠骑大将军,单独带兵,统领一万骑兵,攻打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六天急行军一千多里,重创匈奴大军,与单于的儿子交战大胜,歼敌近九千人,俘获匈奴祭天金人,因功加封食邑二千户。在夏季攻势中,原定霍去病与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兵分两路,攻击匈奴,但是由于公孙敖迷路迟到,未能按时与霍去病大军会合。霍去病果断决定孤军深入,歼敌三万余人。歼敌3万余人。俘虏匈奴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让匈奴的实力受到一次极大的打击,又加封食邑五千户。匈奴浑邪王率部归降,霍去病奉旨迎接,但是部分匈奴降众变乱,霍去病当机立断,率军冲入匈奴中军,将带头叛乱的统统杀死。局势得以稳定,匈奴浑邪王带着四万部众才得以顺利归降。此战后大汉尽收河西之地,西北边境也几乎没有了匈奴的骚扰,使得边境居民得以安居乐业。
古代战争纷杂,动不动就要冲到战乱前线。此时便少不了能力出众能带兵打仗的将军。一个国家的兵力其实便是自己所拥有的筹码,有些事不得不靠武力解决。如果没有过硬的装备和军事力量,他人只会认为这个国家非常软弱,没有什么实力。大可不放在眼里。
历史上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名将,他便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霍去病。霍去病在少年时代就“善骑射”。汉武帝很喜欢他,让他做了自己的近臣侍中。十七岁初次征战即率领800骁骑深入敌境数百里,把匈奴兵杀得四散逃窜。
19岁时,霍去病率一万骠骑出陇西,转战河西五国,与单于的儿子交战。俘虏匈奴王五人,斩上将三名,歼敌近九千人,重创匈奴,一战迫使匈奴后退数里。
后来霍去病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霍去病驰入匈奴军中稳定局势,并率投降的匈奴人斩杀变乱者,浑邪王得以率4万余众归汉。
公元前119年,漠北战役打响。21岁的霍去病与大将军卫青率领骑兵征战漠北。霍去病又率军奔袭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再一次宛如天军下凡。霍去病亲率三千精锐冲击左贤王大营,斩将三名。后大军全军出击,共歼敌70400人,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在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封礼,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封狼居胥。之后又一直追击到北海, 此战为汉朝北击匈奴最远的一次,经此一战,“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廷”,匈奴再也不敢侵犯大汉了,自战国时起的匈奴大患终于解除。
匈奴未灭,何为家也?
霍去病不仅擅长作战,头脑也是非常灵活。他的作战迂回纵深,穿插包围,对匈奴实行合围,他的作战方略可以说是对汉军战术观念的革新。
霍去病的战术了得,但他个人的生活确没有那么圆满。他没有老婆确有一个孩子,是和他府里的一个侍女生的,侍女身份低微,霍去病自然看不上他。后来他便只认了自己的孩子,但也没有尽到做父亲的义务,一直把自己的儿子放在卫青家受教育。
传奇的人总会有一个传奇的结局,当他在战场上获得了多番成就本以为可以一直为国效力的时候,他的生命却就此结束了。23岁便因病去世,让人只觉可惜和遗憾。
那时候的医疗水平有限,霍去病经常在战场拼命,数次出征身体得不到休息,又长时间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对霍去病的身体造成了不可治愈的伤病。
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死感到非常悲伤,他调来由匈奴人组成的属国铁甲军,列成阵沿长安一直排到茂陵东的霍去病墓。他还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彰显他力克匈奴的奇功。
失去了一位这么彪悍的大将,想必皇帝的心里也是说不出的无奈和惋惜。霍去病的一生虽然非常短暂,但庆幸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做出了值得让世人永久铭记的丰功伟绩。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汉武帝同年继位,第二年正式称元,史称建元元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公元前140年),霍去病出生。
伴随着汉武帝继位的历史进程,汉朝国力日益富足,汉武帝决心不再对匈奴退避三舍,刘彻在位的这54年中的43年间,都在与匈奴进行战争,历史的齿轮便是如此的契合,当汉朝不再对匈奴隐忍退让之时,一位能够带领汉军纵横大漠,横刀立马的千古英将应运而生。
他生而不凡,必定命运异于常人,霍去病短短的24年人生,不仅成为汉武时期无法磨灭的常胜荣光,更是千年历史流转之间惊艳绝伦的少年英雄。他用自己短暂的生命,造就汉人将领中最高的荣耀,感染文人墨客谱写最壮丽的诗篇,他唏嘘的一生,如一幅恢弘画卷,就此迤逦飘荡而来。
怒马骠姚将,少年战大漠公元前123年,十七岁的霍去病被汉武帝刘彻亲自任命为骠姚校尉,其中两次追随他的舅父卫青出征漠南抗击匈奴,在那时未及弱冠的霍去病,仅仅被认作是去舅父卫青身边历练,汉武帝也抱持此态。
可是一切都是那般不同,霍去病一入大漠便如鱼得水,展现了他天生的将帅才智,他在经验全无的情况下,再三请兵,亲率八百骁骑在大漠辗转,找寻匈奴营帐,茫茫沙海他果敢智勇,在人迹罕至的漠南精准寻至匈奴所在,深入匈奴营帐数百里,导致匈奴人措手不及,如乱锅上的蚂蚁。就这样,一举斩杀匈奴两千零二十八人,其中包括匈奴单于的祖父和叔叔。给匈奴右贤王和单于主力沉重打击,使匈奴初步退出漠南,向苦寒的漠北退却驻扎。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写道:
“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骠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
初披战袍,少年霍去病便以骁勇之姿莺啼初试,令大漠匈奴为之侧目,于是,一颗新星在这片土地冉冉新升。
但此时的匈奴并不知道,在此后十几年间,这颗赤血将星,将会以迅雷之势瞬息改变两方战局,狂暴地撕碎己方的防线与营帐,匈奴再也不是原本那副狂傲自大的模样。
远隔千里的西汉朝廷也在接到捷报之时,为之大大震惊,虽然汉武帝对霍去病早有赏识,但大约也同大部分朝臣一样,认为霍去病还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小子,需得历练方成大器。可霍去病的所作所为使所有人惊艳,他战马一踏,血刀立横,使脚下大漠风沙翻涌,卷起汉军男儿的满腔热血衷肠。
自此,霍去病不再以皇帝侍中的身份名冠京华,人们所念所想,是大漠之上那一个全新的他——一位年轻的铁血将军,更多的是男儿血性,充血的双眸隼视西北,手中的利剑直指匈奴。
几乎就在这个时刻起,他已被认作是为抗击匈奴而生的,是天降英才,汉武帝喜不自胜,整个汉朝上下都为霍去病镀上了一层金甲,比之舅父卫青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他两次功冠全军,一战封侯,以一千六百户受封冠军侯。
这是十七岁的他,是鲜衣怒马、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郎,也是斡旋千军、统领万马的冠军侯。汉武帝对他越发青睐有加,刘彻也毫不怀疑地认为这个少年是大汉开疆拓土靖安四海的最好战将,所以也努力想让霍去病提升自己。
汉武帝望着身边的少年,叮嘱他务必熟习古代兵法,意在帮助他提高指挥水平,可霍去病却坦然回答:
“顾方略如何耳,不至学古兵法。”
行兵打仗最重要是随机应变,拘泥于古法只能降低军队作战能力,所谓“兵不厌诈”才是好的军队该有的觉悟。
马奔长嘶鸣,刀横收河西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任命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再次出征漠北,这一次霍去病独当一面,直指河西,他带领一万汉军取道陇西,越过焉支山脉,斩杀数名匈奴酋领,后在夏季与战据河西走廊以及湟水流域的浑邪王、休屠王的兵队对阵军前,接连击杀匈奴四万余人,一并俘虏了匈奴王五人及匈奴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等一百二十人。
霍去病因为这一战的勇猛也被史家留下这样的评语:
“诸宿将所将士兵马,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远,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性,未尝困绝也。”
这段话总结了霍去病常胜之因,一为将士、战马优秀;二为霍骠姚敢于深入突进;三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不论什么原因,此战匈奴损失惨重,对于匈奴简直是莫大的耻辱,匈奴大单于大怒,欲对浑邪王、休屠王进行惩戒,这也激起了浑邪王和休屠王的反心。
于是乎,他们在同匈奴大单于俯首求情、虚与委蛇的表示忠心的同时,也在向汉廷抛出橄榄枝,他们频繁派出手下与汉王朝接洽,意欲归降。
汉朝接到匈奴两王的投降意愿,却没有完全相信,恐他们诈降,威胁边疆安稳。霍去病在此时又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以一人之骁勇,收匈奴万马,安汉室之安稳。
在元狩二年的这个夏季,霍去病受汉武帝之诏收降匈奴二王,狼烟乍起的漠南,只听马鸣风萧萧,霍去病一骑绝尘,往匈奴营帐奔去,身后跟着的是血性方刚的汉朝将士,他们带着胜利者的骄傲,也带着军人应有的警觉,只为迎来一场盛大的投降。
他们雄赳赳地踏过大渡河,马蹄溅起浑浊的水花,停驻河畔,远远望去,浑邪王和休屠王的军队上空盘旋着几只雄鹰,霍去病与他的将士们没有任何胆怯。几乎只是瞬间,霍去病即做好部署,率领一支亲兵队伍直冲入匈奴营帐,他杀伐决断,与浑邪王联手诛杀八千名不愿归降的逆兵,又派军队亲自“恭迎”浑邪王前往长安朝见汉王,亲自带领归降的匈奴将士渡过黄河进入汉朝的领土内。
就这样,几乎未费一兵一卒,霍去病便稳定了河西战局,开辟了汉武帝疆域大一统的新征程,从此汉朝控制河西地区,为打通了西域道路奠定了无懈可击的基础,匈奴对霍去病愈加恐惧,霍去病以睥睨大漠之态傲立世间,也如微凉刀剑剜进匈奴心上。
此战后匈奴地区开始流传一首悲歌: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藩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此战后,汉朝全朝上下更是将霍去病奉作汉军“军魂”,汉朝万千将士在霍去病麾下,便如同是有了神明护佑,常胜无败。
封狼居胥山,成“不灭战神”霍去病通过此前数次战役,已在九州之内四海之中立下威名,匈奴虽然胆颤心寒,却仍然不肯让出大漠,使之尽归汉王朝,他们企图将匈奴大单于的牙帐和主力部队尽数迁往大漠之北,利用漠北天时地利的优势,继续抗击汉军。此时的他们心中还存侥幸,欲利用汉军不熟识大漠地形作战滞后的劣势,一举击败汉军。
但是他们忽略了霍去病的作战天赋。就是在公元前119年,霍去病为汉朝锁定胜局,这一年春天,汉武帝为了自己的大一统政略,发动了空前绝后的大规模伐匈战争史称“漠北之战”,他派遣卫青、霍去病前往大漠以北抗击匈奴,数十万铮铮铁骑奉旨北上,他们都目光如炬,气势如虹。
假使这一战能将匈奴彻底打败,汉朝将成为天下主宰,他们的家人不必再四处流离,海清河晏,必将是一片祥和。
将士们追随着他们的将军霍去病,更追随汉武大帝的指向,再次踏入大漠。霍去病已然成为了这一方天地中最强势的存在,这里是匈奴的修罗场,这里是匈奴的阿鼻地狱。
霍去病依然发挥着他出神入化的战术,辗转于万里漠地,追寻匈奴主力,一路厮杀,奔袭两千多里,损失汉军一万五千多人,换得歼敌七万多人,俘虏匈奴贵族三人以及各级军官数十人的战绩,这样傲人的成果,只能让匈奴狼狈逃窜往更深的大漠腹地而去。
霍去病大概仍然不满足这样的战果,他坚守着自己“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誓言,带着汉人的血性,一直将匈奴赶杀至今蒙古肯特山一带。
“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瀚海而归。”
霍去病于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封礼,于姑衍山举行祭天禅礼,此举成为后世无数英雄将军,穷尽一生也无法追赶的一个梦想。
此战后,匈奴被汉军在漠南荡涤一清,于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的格局就此奠定成型,成为了汉室抗击匈奴以来的顶峰,匈奴再也无法对汉朝带来多少威胁,而汉室几百年来,迫于匈奴的压力,被动纳贡、和亲等的屈辱,也一并消失在了大漠的缕缕烟沙之中,
霍去病成为匈奴人心中磨灭不去的业障,他是死去的万千匈奴人的戮杀者,却是汉朝百姓的保护神,他还是那个翩翩少年,更是一位民族英雄。
今后,匈奴再也无力与汉王朝对抗,霍去病的使命也就此完结,他回到长安,长安还是年少时的长安,繁华如烟,眼前只有“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长安是霍去病一生最初起步的地方,这里有他“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心壮志,汉武帝对他只有器重,再无其他,这个二十多岁的生命,成为了整个国家的精神所在。
将星悲陨灭,后世传神话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得汉武帝赏识,官至大司马,同他的舅父卫青同位,骠骑将军的官位与俸禄也与大将军之位相等,仅凭军功,世间再无人能及霍去病。
天可降英才,可天也妒英才,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猝然离世,成为千古之谜。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病死,有人说是卫氏一族谋逆陷害了霍去病,真相我们无法探究,但在霍去病死后,汉武帝异常悲伤,这个死去的少年不过24岁,汉武帝看着他长大,如今看着他死去,他的人生本不该如此薄命,却终究难逃天命。
死后的霍去病陪葬茂陵,谥封“景桓侯”,这两个字取义“并武与广地”,以彰显霍去病克敌服远,骁勇善战,为汉朝扩充疆土之意。
汉武帝调来玄甲铁军,排列成阵沿着长安蜿蜒到茂陵东侧的霍去病墓,并且下令将霍去病的墓葬修成祁连山的形状,以此显示他抗击匈奴的功勋。汉武帝生前将他托举至军中至高位,死后令他常伴自己,恩泽至深足以明见。
霍去病,这个名字至今读起来,还是如此举足轻重,他是千古英将,因为他的骁勇善战,因为他的杀伐决断,匈奴对他闻风丧胆。他用他24岁年轻的生命托举起汉朝至上的荣耀,他让匈奴从此退出中原舞台,远走大漠。“饮马瀚海,封狼居胥。西规大河,列郡祁连”。
有人说,霍去病是历史上最让人惋惜的存在,假使他能再多活二十年,可能整片亚欧大陆的格局都将不同,历史上军事最让人瞩目的存在或许不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由霍去病带领的汉人。
当今社会,金钱与浮躁风气并行,已是鲜有人关注历史,不久前动辄还有“历史人物卫青、霍去病被初中历史教科书删除”这样的话题,或许在今天的和平年代,霍去病已然没有多大用武之地,然而如果有人温习那段历史,书卷之中,那个被誉为“汉军军魂”的魂之所在,神之所在的少年也仍在熠熠闪耀。
历史长河中席卷过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人声色犬马,有人碌碌无为,有人怀才不遇,可霍去病在历史上唯此一人,也许他不如那些情史秘闻惹人心痒,亦不如那些迁客骚人扣人心弦,他的故事稍偏热血激昂不那么政治正确,可也最为荡气回肠。
本文地址:http://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97691.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douchuanxin@foxmail.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李固—东汉著名谏臣
下一篇: 东汉时期的年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