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只有不到1%的人关注我们
你真的很特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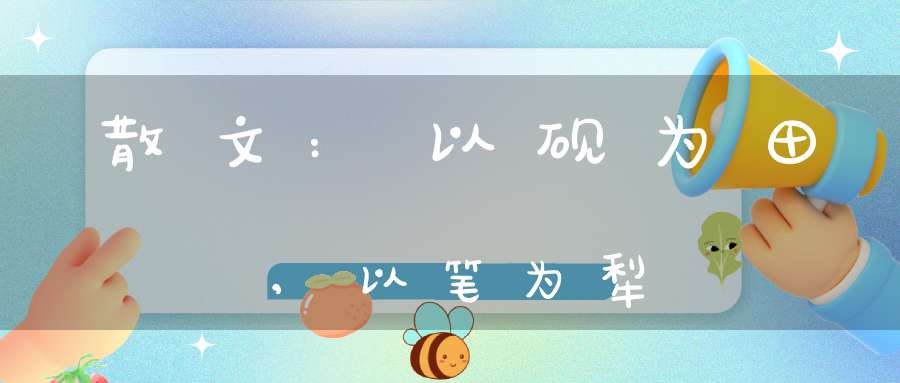
写在秋季
2021-10-12
人握着拳来到这世界,仿佛是说:“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但在离开人世时,人都是摊开手掌,仿佛是说:“看吧!我什么也没带走。”笔
文/陈巽之
一枝笔能做什么 它能产生多大价值 其实,笔本身没有多大价值,即使是一只世界名牌的“派克” 牌钢笔,也不过几百元钱。笔杆只有数寸长短,被人称为“寸管”,用来打狗不如一根木棒,笔的价值在于它的使用价值,笔的力量在于使用它的人。
笔在有的人手里被用成了刀枪,最长此道者首推清代官场的“绍兴师爷”,他们被称为“刀笔吏”,当官的要想在尔虞我诈的官场应对自如,最重要的就是要聘请到一位好的师爷,他们可以摇动如椽大笔,值你的对手于死地,笔在他们的手里可以杀人,也可以活命。曾国藩在湖南同太平军交战,累战累败,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如实写道:“臣累战累败……”他的师爷看后建议他改为“臣累败累战……”一字之改两重天,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朝廷的责罚,而且还受到嘉奖。
毛泽东曾在一首词里写道:“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他作为人民军队的统帅,从秋收起义的枪声到三大战役的硝烟,经历过无数的枪林弹雨。他虽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但一生从不配枪,相反他一生没有离开笔杆子,在戎马倥偬之间,战场硝烟之余,他手不停挥,笔惊风雨,横扫千军如卷席。在文化上,以一首独步千古的“沁园春·雪”就让将介石及其御用文人尽折腰。在军事上,他用笔杆子草拟作战命令,在西北坡的小山村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谈笑间就使数百万国军灰飞烟灭了。
写在回忆
有一个作家曾写过一篇文章名叫“以笔为旗”,这谈何容易,作家或者说文化人都有一枝笔,要将一枝笔挥舞得呼啦啦作响,如一面艳红的旗帜迎风招展,吸引过往的行人以为同志,这不是一般作家所能为之。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只有两个文化人能以笔为旗,一个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他标榜“文以载道”,举起如椽大笔,一扫当时文坛上的绮丽柔靡之风,以清新的文风别开生面。另一个应该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尽管毛泽东曾将旗手的封号给了鲁迅,事实上,真正的旗手应该是陈独秀,想当年风华正茂的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文学革命论”为宣言,高张“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三大主义为旗帜,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掀起了狂飙突进似的文学改良运动。除此二人之外,我没有想到还有谁能以笔为旗了,如果有谁认为自己手中的笔是一面呼拉拉作响的大旗,那是多么的狂妄和不自量力啊。
笔作为一种书写的工具,和农民手中的犁,工匠手中的锤一样。我早年就同文字结缘,大半生靠笔杆子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很长一段时间,笔就成了我的衣食父母了。我喜欢听笔尖在纸面上划动的“沙沙”声,很多个夜晚,万籁俱静,妻儿也睡熟了,我“夜深独对一灯红”,对着洁白的稿纸,写下一行行诗歌,这时候笔下的“沙沙”声,就成了最动听的音乐,我乐于享受这样的夜晚。当然,为了饭碗,我要写许多我不情愿写,又不得不写的文字,这样的文字,让我感到别扭和痛苦,恨不得把手中的笔一折两断,不再写这些让我痛苦的劳什子了。但是文人积习,往往好了伤疤忘了痛,一天不摸笔杆,就好像缺了什么东西似的、魂不守舍。
有人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聪明人是干不了这种心力和体力双倍付出的苦差事的。我自己既没有韩愈的才气,也没有陈独秀的霸气,绝不敢标榜以笔为旗,更不敢谋虎皮为大旗,吓唬别人。我情愿像农人在土地上耕作一样,把我手中的笔当作农人手中的犁,蘸着自己的心血老老实实的书写文字。我不期望自己能成为诗界的李白杜甫,不期望自己能成为鲁迅第二、莫言第二。但我愿意像路遥学习,“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种子播种了,汗水流下了,也许能开出一朵小小的花,结出一个小小的果。
倘能这样,此心足矣!
写在回忆
作者简介:
陈巽之,原名陈家顺,贵州威宁人,现居西安,大半生执笔弄文,结缘文字,多次在全国诗歌、散文大赛中获奖,己出版诗词集《鸿爪雪泥集》、散文集《苔花米小牡丹开》、长篇小说《几度秋凉》。
记录生活 扩展阅读 原创原创散文:荷散文精选:夜未央原创散文|给我一片天(原创)原创原创诗歌:秋韵叠章原创散文诗歌:爱的絮语(原创)聆听|戴望舒散文诗歌:十四行,雨巷,狱中题壁
散文精选大全
「最受欢迎关注散文精选大全,邂逅诗歌散文」
诗词 |朗诵| 短片 | 散文| 段子
品散文,阅人生
散文诗精选朱自清散文基督教诗歌诗歌朗诵爱国诗歌
唐之世,文人雅士,多以澄泥为四大名砚之首。澄泥实为汉晋陶砚之余响流韵,而又优于陶砚者。
澄泥砚的好处,在其质坚密、其体轻盈,不损笔,易发墨。古人论澄泥砚的优劣,认为以虾头红为第一,鳝鱼黄为第二,茶叶末次之,绿豆砂又次之。然世间鳝鱼黄与茶叶末两品多见之,虾头红澄泥砚却十分稀罕。重鳝鱼黄澄泥,是由于它特别坚实细腻,烧制时的温度把握得恰到好处。但无论哪种颜色,均非人工故意为之,而是由于烧制时温度不同罢了。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曾在《砚史》中盛赞澄泥为“砚中第一”,说是“叩之金声”、“刀之不入”。“刀之不入”是说澄泥砚坚致得可以试金铁。而上好的鳝鱼黄澄泥砚,可以手触之生晕,与大西洞水岩端砚相类。
澄泥砚除了质地与端、歙石砚接近外,其色彩也非常美观悦目。朱砂澄泥色如红玫瑰;茶叶末澄泥素雅沉静;鳝肚澄泥色泽金黄。
在工艺上,由于澄泥砚的材料是很细腻的河泥,在烧制前后均可以发挥想象力与艺术创造力,进行雕、琢、刻、划,所以形制能够丰富多样,雕功可以精美绝伦。
根据有关砚史记载,河南虢州 现灵宝及豫西一带 首先出现澄泥砚。宋代李之彦说:“虢州澄泥,唐人品砚以为第一。”还有一种说法是澄泥砚始产于山西绛州。另一说是产红丝石砚的山东青州 今柘沟镇 。
但不管是虢州、绛州,还是青州,澄泥砚制作工艺的流程也是大同小异。它的制作方法,大约是将一个绢袋缝好,再扎紧袋口,用东西固定后沉入河水中,一年或两三年后,袋内已贮满细腻的河泥。将袋中泥取出后,“入黄丹,团和溲如面。作二模如造茶者,以物击之,令至坚。以竹刀刻作砚之状,大小随意。微阴干,然后以利刀刻削如法。”而后,在日光下晒干,以稻糠抖和黄牛粪烧制,到火候,再掺以黑蜡、米醋、“蒸之五七度”。如此繁复的制作工序完成后,澄泥砚才会有其坚可试金铁,润可留手晕,并达到起墨益毫的效果。
出土和传世的古代澄泥砚,较之端、歙等石砚要少得多,尤其唐、宋二代的遗物,更是难得一见。
笔者曾于一藏友处得见一晚唐澄泥砚,为唐墓出土,箕形,背有一卧足、两扁足,长仅四寸余,色作茶叶末,叩之如磐,知其质地坚密。此砚在日光下视之,有细碎光点,均匀而细密。可能是古人所说的“黄丹”或“丹粉”。这种东西就是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配料 我曾看到葛咏岚先生一篇写宋代澄泥砚的小文,文中认为唐宋明三代澄泥砚大抵除了主要工艺相类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泥中配放了“丹粉” 亦即黄丹 ,而这种“丹粉”即云母粉。云母粉的颗粒要很细,这样才不会被同行发现秘密。这种说法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根据我的分析研究,唐宋明三代,所配云母粉的多寡,似乎都不一样。唐代澄泥砚中往往可见紧密排列着的云母小颗粒,宋代澄泥砚的云母粉少于唐,明代又略少于宋,且明代的颗粒细如粉尘,这是明代制砚讲求精益求精的表现。
笔者有一方“古井”澄泥砚,明代之物,色作鳝肚黄,呵之成雾。砚盒以整块金丝紫檀剜空,砚与盒正方形,为16×16厘米。此砚对光侧视,可见极细的银色光点,均匀排列,呈熔融状态。可见古人制澄泥,为何定要加添此种云母成分的奥秘。我以为除了一系列工序的不可稍有差池之外,火候与云母粉,应是一方澄泥砚能否达到起墨益毫与美观悦目的`关键。
有没有不加云母粉的澄泥砚 回答是肯定的。清代澄泥砚的衰微,我以为除了石砚制作更为便利之外,古法失传恐怕是主要原因。古法失传,作出来的砚就无法与明以前的质量相比。乾隆虽曾下令制过澄泥砚,效果总不如人意,后世更有不逮。湘省藏家游先生收藏一件清代“九如”澄泥砚,体形甚巨,长达一尺有余,遍体刻蝙蝠与螭龙纹,砚背刻写九个“如”字,称“九如”澄泥砚。色青黑,质地坚密,以手抚之,润而不嫩。对光侧视,未发现云母粉颗粒。这方大砚,以益毫发墨的标准评价,品质只在中等,比之明代鳝肚黄、虾头红之品,相去较远,砚为清代乾嘉年间制作。很显然,澄泥中若不加添古人所说的丹粉及有关配料,是很难达到端石或洮河石等有关优材石砚的水准的。所以清代至民国所产的澄泥砚台,往往不为鉴藏家所珍,这就不难理解了。
澄泥砚从实用与鉴藏的角度来看,都十分独特,它曾经冠绝一时,是很有道理的。它制作工艺的繁复性与秘密性,品质与色彩的独特,都较之石材砚品毫不逊色。以笔者的观点来看,一品鳝肚黄可抵十方中等端石。此言若海内方家点头认可,则笔者必引为砚中知己了。
散文朗诵:落笔成文
一支笔,束之以狼毫,始已两千余年,雅号彤管,始祖蒙恬。其大笔如椽,可载得千秋岁月,可建构灵魂的层楼。
一抹飞白,在黎明的前夜,划出一道霞光,散发了墨香。
子夜的灯影,萦绕笔墨纸砚,梨花般白的纸页上,玄圭染霜,化为文字启明的热度。
天下世象风物,工笔描绘出了封尘,墨韵流连落在笔端,便寰宇一页,天头地脚,阅尽人间万世。
陈年的冻土,犁开思想的火花,毫末锋芒,去收获了金秋。于尘世朦胧中书写一次次人类的阅识和心智。尊严洇染纸上,神圣的涂抹,不让玷污了黑白。
山断崖,水苦涩,一条石阶小径,留下一联励志的千古警言,唯其不可缺。勤为径,苦作舟,直挂云帆济沧海。
我背起行囊,犹是苦行僧的行径,握一支秃笔在手,着墨,留白,照着葫芦画瓢。
见了古来士林大家者,皆神闲气定,运笔走锋,着墨间密不缝针,留白处疏可走马,审美志趣发于毫端,而惊风雨泣鬼神。
蘸笔岁月,挥毫春秋,流年何处不墨香。此中有花好月圆,书剑恩仇,浪漫与锋芒,卑微与荣耀。一点一划,横竖撇捺,自是苦乐悲喜,美丑善恶,落花呻吟,鱼虫絮叨。
一笔一纸,一砚一墨,君伏案头一片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湖海,帝家庙堂文士风骚,全是笔下取来,纸上成就。
方块字,中国画,诸子百家诗词歌赋,二十四史鳞言爪语,文明的厚林,峰峦陡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莫延宕,时光正好,两千年过去,落笔一挥间。涂抹了几笔,就一个流芳浩荡的风云青史文明盛典。顺便涂鸦我一纸浅唱,说了些私话,和梦语。
将生活研磨一方浓砚,且把狼毫饱蘸任挥洒。端的是笔力三冬方透纸。君不见,寒窗月色老,砚池成墨海;君不见,洗笔潭前,树已成荫。
本文地址:http://dadaojiayuan.com/scgf/105108.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douchuanxin@foxmail.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散文|WC王妃
下一篇: 夜读散文邱少云:烈火中永生